专访尹稚:城镇化下半场,如何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”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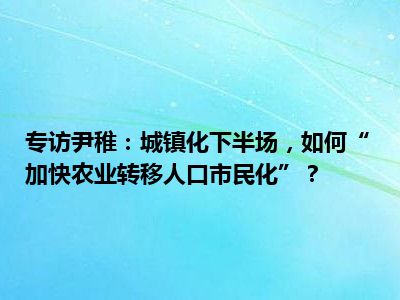
在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,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“钱”的问题。一方面,需要厘清成本如何分摊;另一方面,需要明确中央财政优先补给谁。
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23日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专访时,提到了上述观点。
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(下称《决定》)中明确提出 “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”,并将其作为“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”关键环节。
《决定》还多处提及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权益保障,比如“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,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、住房保障、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。”
“‘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’已经试点多年,但一直没能在全国铺开。其背后关键原因在于,‘中央财政支持谁’的问题没有解决,是均匀地‘撒芝麻’?按行政区划的盘子大小去配给资源?还是按人口流入强度给予资源倾斜?”尹稚说。
在他看来,在“农民转变成市民”的过程中,需要算一笔账。“转移”的成本由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、用人单位和转移人口个人四方分摊。其中,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是地方在做成本核算、规划基本公共资源配套时考虑的重点。
尹稚说,新型城镇化的上半场,我国已经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市民化进程中的阻力因素,打通了市民化的法定和关键环节,取消了户口迁移门槛。目前,这些群体已被纳入地方核算“城市人均拥有基本公共服务”的分母,在进城务工人员持有居住证的条件下,其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从早期的6~8项提升至20多项,甚至在一些发达地区已接近户籍人口的待遇水平。但农村转移人口所拥有的基本公共服务优先级还不够,隐性的歧视性政策还没有解决,其社会保障水平仍低于户籍人口,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资金投入。
据尹稚介绍,过去,中央财政对“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”的投入,大体可以分为两类:一类是“补砖头”,即按照城市规模和整体的建设量配给资源,至于新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没有人用,“其实没人操心”;另一类是“一刀切”,即设定统一的基本系数,根据行政级别,按照城市扩张规模的一定比例,分配资金。但上述两种投入方式均可能带来资金浪费或投入不充分。
《决定》在“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”中称,“把握人口流动客观规律,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,促进城乡、区域人口合理集聚、有序流动”。尹稚认为,这给出了接下来中央财政投入的一个方向,即“补人头”,人往哪里流,哪里获得的份额就更多。下一步,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央地之间投入比例。
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越高,人口流动性会越大。当村镇人口的活动半径扩大至都市圈,他们获得的岗位机会也越多。换言之,完善符合现代人口流动的配套机制,还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充分就业。”尹稚说。
按照人口流动方向,热点一二线城市或将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,用以完善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”的公共服务。这些城市原本经济发展水平就相对更高,那么,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否会因此被拉大?
尹稚认为,首先,用于推动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”的中央财政专项拨款,总量不会太大并会专款专用。相比之下,中央财政每年会在平衡区域发展方面,投入更多资金。其次,在一些生态保护地区和农业主产区,这些地区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能力还很弱,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。“换个角度看,如果这些地区能够真正将粮食安全做好,生态安全守好,获得的收益远比流失人口带来的损失要大。此外,一定程度上的人口流出,也有利于这些功能区的集约化发展。”尹稚说。
出于成本考虑,县城往往是农村人口“从乡进城”的中转站。近年来,中央多次强调“县城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”。尹稚认为,在未来人口分布中,可能县城所占城市化人口比例并不是最高,但它具有重要的节点作用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年政府在乡村全面振兴中投入了大量资金,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。
根据《决定》,引导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、集约紧凑布局;深化赋予特大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经济社会管理权改革。
尹稚表示,镇一级政府部门的传统行政职能不足以支撑其经济和社会管理,可能会对特大镇的经济发展形成障碍。“但《决定》没有提到‘撤镇设县’,意味着未来更可能在行政区划不变的基础上,赋予特大镇更多经济职能。我认为未来县级单元在数量上不会越来越多,以免造成国土空间的分散化和破碎化,但经济社会管理权可能会进一步下放到特大镇。”尹稚补充说。
此外,在尹稚看来,进入新型城镇化下半场后,“人”应该能够自由地在城乡之间,双向流动。这意味着城市地区“居住证”和“户籍证”的差异越来越小,大城市有能力承接住更多“农业转移人口”,也意味着“从城到乡”的人口反向流动渠道会进一步被打通。
《决定》也再次重申,要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、双向流动,缩小城乡差别,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”。
“但现在‘从城返乡’的渠道还没有完全打通,大城市人口返乡缺少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。目前城乡之间在土地政策和行政管理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。在新型城镇化的下半场,还需要为这些返乡人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,让他们在农村也能获得身份认同和权益保护。”尹稚说。














